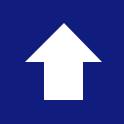每一位蒙台梭利学校儿童的父母都不可避免地会问,当他们的孩子从一个蒙台梭利教育机构毕业,最终进入常规的教育体系或大学后,孩子们的表现会怎么样。Rebecca Makkai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她13岁从蒙台梭利小学毕业后,进入了常规的中学。高中毕业前夕,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了她曾经接受过的蒙台梭利教育和对她生活的影响。她计划到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并准备将来从事写作事业。以下是她的叙述:
在我最初几年的蒙台梭利学校生活中,给我留下了最深印象的一项实验是“细绳上的捅”。我还记得,当时我站在一年级教室的门口偷偷地向里面张望,观看着那些“较大的孩子”。他们正拿着装满了水的锡桶,将一根细绳绑到锡桶的提手上。然后,让我非常吃惊的是,他们提起了绳子并且开始在空中以很大的环形轨迹甩动锡桶。正当我准备跑去向老师报告这种“可怕的行为”时,让我更加吃惊并被我认为是再神奇不过的现象出现了:水停在了桶里。几年之后,我自己也做了这个实验,并且知道了这种神奇的现象被称为离心力现象。重力并没有消除,只是被超越了,水具有这种神奇的特性。
帮助我学会如何表演这种“神奇现象”的是我的老师,她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做了演示—一件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具有着最崇高地位的事。那一刻我们知道了,我们也是能够理解那些“大孩子们”已经知道了的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就像“飞舞的水桶”一样。
这些展示的确是在将世界逐渐呈现给我们。在我5岁那年,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向我们宣布,教室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有一个名字,她向我们发出挑战,看我们是否能找出一件没有名字的东西,我们没能找到。然后,我们开始学习教室以外事物的名称—草坪上各种树木的种类;树上叶子的种类;一个苹果的各部分名称;一只蜥蜴的身体各部分的名称;我们国家各个州的名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名称等,我们还了解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责任和角色。我们看到了在长长的年代表末端那个代表着人类的微小轮廓,我们知道了那就是我们。我们看到了一盆盆植物和生活在角落洞穴里面的地鼠,它们需要我们的照顾。
我们看到了要作的画,要写的剧本和要解剖的昆虫,我们因此变成了画家、作家和科学家。
既然世界被呈献给了我们,我们也随后将自己展现给了世界。在蒙台梭利学校,我被允许参加创作展示会,它是用来激发我们短暂的兴趣和激情的。令人吃惊的是,老师们就像当初我接受他们的展示那样接受着我的展示。他们耐心地坐在那里观看我们冗长的幽默小品和更长的报告;他们还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争先恐后地要讲给他们的故事,即使他们知道那些故事不是真的。
我们被全力地鼓励着去进行创造、实验和探索,我发现我在小学四年级时所得到的自由甚至比我在高中高年级时所得到的还要多。
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很早就认识到,蒙台梭利教师给予了我们毫无保留的信任,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我们自己选择的事情,从可以自由地挑选教具到可以在教室里自由地行动。我难以想象,如果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谈话和行动的权利,我的教育将会是怎样的不同—就像
那些在其他学校上学的我的朋友那样,视老师为监视者而不是朋友。
在那种将“你敬一尺,他们就会要一丈”作为信条的教育中,这种信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蒙台梭利教师们给我们的是“一丈”,而且,正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足够的信任,我们也将用尽全力跑完这“一丈”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尊敬。这种动力还支持着我经历了整个的高中阶段,它已经根植在我的内心深处,并成为自尊,这种人的自尊
推动着我不断地去超越,超越我曾经为自己设置的各种目标。
在科学领域我所接受的第一个展示是关于固体、液体和气体特性的。我们被告知固体是稳定的,气体是无形的,而液体则可以自由流动的,以便它适应容器的形状。儿童就像液体,他们塑造着自己以适应放置他们的容器。在能够自由走动的地方,他们就走;在能够动手做的地方,他们就做,拥有了这种自由,他们就不会再感到有冲破束
缚的需要了。
儿童因被信任而变得生机勃勃。当被允许步行到城镇中去时,他们就会出发;当被允许描绘一幅图画时,他们便会动笔;当被允许用数个小时去掌握动词转换规律时,他们便会愉快地沉浸其中。我将永远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他们给一个小孩子的不可思议的绝对信任。(刘文,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心理学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点学术带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士后。现为中国蒙台梭利协会终身教授)